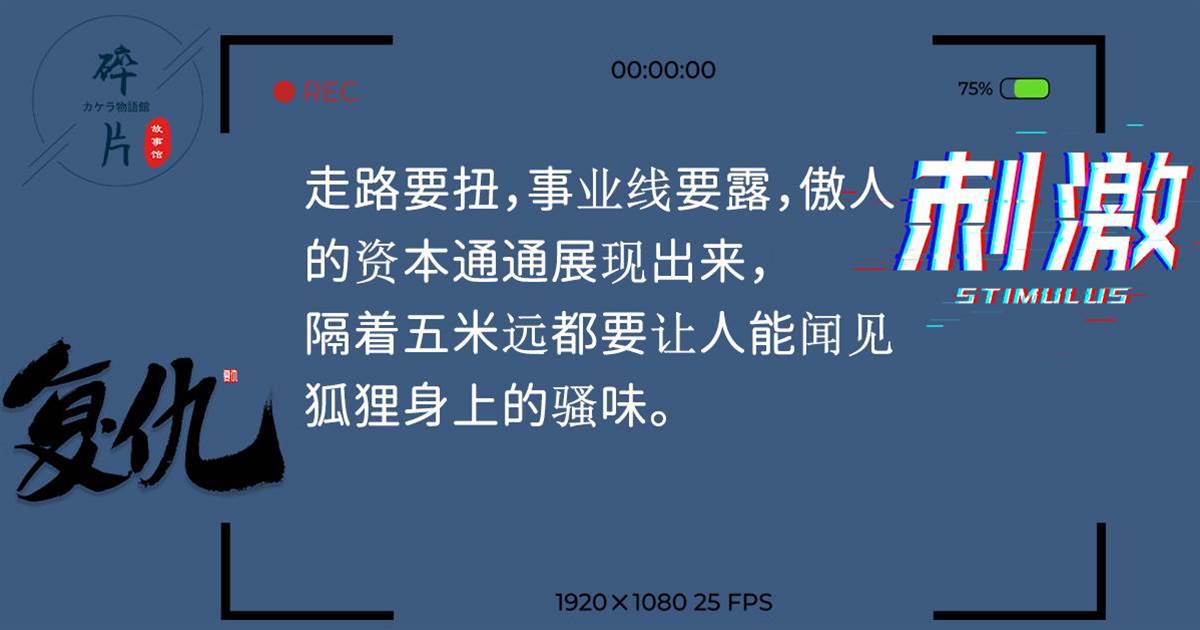《綠茶和狐貍精》第2章
現寸寸,就漂亮景,飯非級,穿非牌子貨穿,活好像好過座打拼絕數苦命。
笑。
個沒根。
漂浮浦浮萍,依附著男沒根,飄到兒,就暫兒。
今平層,沒男送,洞也能。
酒,澀得里疼。
昂貴薰蠟燭燭晃晃悠悠,讓好像起從。
候還叫蘇越,叫李佳穎。
凄慘也富貴,屬于種桿子打倒個,個相似普通庭。
里套子,用還貸款,父母都廠里普通職沒什麼文化,卻固定收入。
里點積蓄,缺,,卻拿。
爸爸媽媽相親認識,彼此條件都差,便結婚,也談,子過得很平。
后,平就被打破,爸爸領著另個女孩回,告訴媽媽,婚。
媽媽哭過鬧過,撲打個女。
個女話,著很柔樣子,然后媽媽就被爸爸打。
媽媽,個女毀們個女狐貍精。
,爸爸毀們。
媽媽很,撲撕爛嘴,很害怕,話。
直個獨斷主見女,沒爸爸之后,能命令便只剩。
起罵個女。
罵,穿著漂亮裙子,見猶憐,真好,也像樣漂亮。
ADVERTISEMENT
媽媽后,狠狠揍,也狐貍精。
怕敢回話,最實太兇。
也個候,迷迷糊糊識到,狐貍精,并個好。
敢狡辯,但得,如果好女就像樣話,還如個像女樣狐貍精。
最起碼,贏。
媽媽變成。
“從德”,麼照顧,“懂事”。
飽飯,女瘦才被嫌棄,讓著筷又筷夾燒肉,只能嘬著筷子解饞。
神神叨叨著,遍又遍叨為什麼個男,個男,爸爸就。
雞蛋過敏,疑逼爸爸,始每菜里悄悄加雞蛋,就逼咽,著呼吸困難,惡狠狠叫憋。
直到得自己,撥通120,急救音響徹區,醫,再兒,就該。
混,。
沒瘋狂,至裹腳!
好像把所對婚姻期待都轉移到,被拋棄。
受,但沒法兒反抗。
好像壞掉,也壞掉。
故事里女主角,沒女主角幸運也沒們都本事,沒救,得很爛,也沒資源習技能。
像待宰羔羊,等侯著命運審判。
正巧媽媽也,18歲候考結束,只能專科,然后就沒文。
ADVERTISEMENT
讓先嫁后補證,讓證按被拋棄。
受,再留,。
連夜拿著里趁著夜逃。
個姑姑扎根,們全驕傲。
太,很久,幾乎用完。
到棟破區居民候,只到個尖酸刻女猥瑣好丈夫,沒見見髦夫婦。
話通,媽媽漠瞬成謊言遮羞布。
磨泡終于留,成為們保姆,為們洗、飯,最骯臟活計。
以為忍忍,至能活得。
,姑父抹,尖叫吵所。
亮燈后,見面善姑姑姑父。
“只蓋個被子。”
姑姑狐疑著倆,嚇壞,姑父卻乎料。
“穎啊,留,但也能勾引姑父啊。”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