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
皇子徽印用途何止庫。
與都肚。
「再麼也父皇過賞侍妾,沒娶正妻沒納側妃,個皇子府里除就最,難今親賞侍妾,還抵得個宮赴宴資格?」
帝后傳言囂,于圣易儲消息更傳得子。
皇后牢牢把持著宮。
而太子作則越加急,里暗里往禁軍里塞自己。
如今宮賞宴,臣聚,自然權力交接最好。
斂笑,斥責胡鬧。
搶之馬。
「吧,放。」
都托,都借。
怕今夜真變故,怕蕭元初失敗,也依然辦法逆轉切。
就再次回原點,蕭元初再記得。
又什麼系?
陪邊,直到最后刻,論如何。
就夠。
53
「皇后父皇藥。」
帶完,悄無息退邊。
彼帝后俱未席。
倒太子首,遙遙沖著蕭元初舉杯示,兄友弟恭戲。
蕭元初舉舉杯子,借著袖袍掩,悄悄與消息。
「御醫院剛遞話過,父皇概撐過今。」
識抬往御座望,又被蕭元初把按。
「替倒酒吧。」
「都教麼久,麼還沒把緒藏好點?」
借著袖遮掩,拍拍。
「既然太子疏通系送宮,現又跟邊,自然格注,緊。」
掌干燥,似乎種神奇魔力,撫本應該現緊張。
已經迅速衰老帝王幾乎被皇后宮架著抬御座。
監替子唱宴賜酒流程。
昔威嚴子如今就像個失傀儡,勉端,卻只能任擺布。
子適,皇后自然而然接管本該由完成賜宴。
卻皇后第次端起酒杯,原本還垂著圣,突然顫顫巍巍站起。
異變陡。
太子搶步,扶圣,驚叫。
「圣咯血,傳御醫!」
守殿甲軍魚貫而入,刀執仗,將殿塞個滿滿當當。
圣似乎已經力竭,扶著太子喘息半,才伸袖子,擦嘴角血跡。
「麼,御醫今全改穿盔甲?」
「什麼候改規矩,麼朕都?」
殿里群臣屏息,都等著站權力最點兩個分勝負。
太子被圣噎,原本話頓便。
猜太子原本計劃,由御醫當眾宣布圣無力回消息,再由甲軍封子易儲向。
畢竟個已經能夠再話帝王,沒辦法當眾易儲決定。
只子提易儲,太子就唯被承認繼承。
無能夠提質疑。
但很顯,現圣僅沒適到太子預期狀況,至還能把話講到讓群臣都步。
蕭元初垂。
子松,把推太子,順帶掀自己面子。
「皇后懷軌,圖謀反,竟指使宮朕毒,若非吾兒元初細,朕幾欲為毒婦所害,太子皇后所為,加制止,反助紂為虐,如此腸歹毒,孝悌之,配繼承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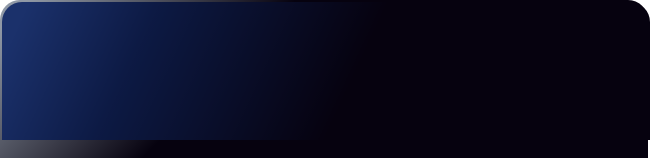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