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問,名字。」
瞬恍惚,封已久答案沖而。
「如。」
具原本,陸隨取,更周越替捏造。
屬于自己,除沒任何,也沒任何,本名字。
實太,到讓至已經忘記,自己本名字什麼。
對面向伸,與掌交握。
微微用力,把拉起,對面。
「好,如,叫蕭元初。」
陽從馬半卷簾灑,往喧囂瞬仿佛被按暫鍵。
全世界于而言,似乎只剩馬蹄清脆噠噠,還著里清澈又熾芒。
50
蕭元初講個故事。
個女子以為遇到故事。
女子平于個世對于女性苛嚴與打壓,竟然異,頂別名字,女扮男裝,以區區平民份混入科舉,考入殿選。
然而運也僅僅止步于殿選。
現冒名頂替,當揭。
謊言被戳破,卻絲毫懼,當著君王面,引經據典,若懸。
對于帝王而言,樣女子,無疑種奇驗。
文章成與始見證,再無于其。
從此榜個滿懷壯志舉子,后宮個滿腹才華妃子。
陪著,之,從品才封至無兩貴妃。
賜最繁華宮,最珍貴珠寶,任由異胡鬧。
愿女子能囿于宅,便官宦之廣選女史,充入宮,陪解悶。
愿宮女能枝依,便改律令,以宮女愿宮者,賜返,自聘嫁。
愿女子能識文義,便修崇文館,請夫子每講,宮閑暇皆講。
言官議論彈劾,盡數壓理。
直到為皇子。
全全教養們孩子,得將自己所傾囊相授。
卻當鮮褪之后,藏于潮底礁便嶙峋尖角,撞得破血流,至命喪當。
皇帝終于才之,現碰皇權野。
皇后精準抓皇帝與之嫌隙,聯朝臣集難。
帝王之種種寵與特權,盡數化為刀劍,成罪孽,反噬。
變成個宮能提禁忌。
所于痕跡被抹。
宮再招收女史,宮女再被允許,崇文館被廢棄。
曾經君王駐流連宮逐漸荒蕪破敗,名字被所遺忘。
唯留,里流著半帝王血液個孩子。
受過恩惠宮女史盡力保全宮。
然后代換。
「誰嗎?」
蕭元初引著完座皇子府。
「穆貴妃。」
「貴妃盛寵之,怕宮都能直纓其鋒芒。」
嘴角彎起,帶著無盡惆悵與孤獨。
「母妃。」
51
蕭元初把皇子府里最好留。
似乎對著種乎偏執放任與期待,什麼都避諱。
由著府里逛,至誤闖候,依然讓繼續匯報自于宮線傳回消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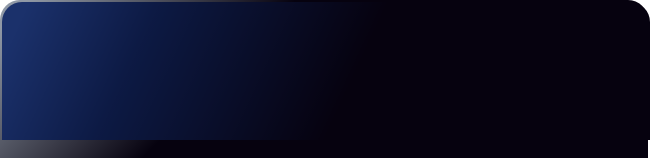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