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連改變自己結局都到。
再甘又什麼用?
男目直落,目探究之太過于骨,以至于突然煩躁。
「什麼,什麼好。」
抓起袍沖狠狠砸過。
然而太,胳膊又夠,袍連都腳尖都沒碰到,就飄飄落回。
男卻像到什麼奇玩兒樣,忽而笑起。
「怕。」
打量著,直接結論。
然后又問:
「誰嗎?」
應該什麼。
應該刻跪磕請罪,對奴婢識泰沖撞貴。
但。
皇子又麼樣,太子又麼樣,皇后又麼樣?
過次之后就又跟歸歸。
于干脆沖翻個。
「,誰誰。」
就笑得更。
得怕碰到個瘋子。
以份,個代,對任何事,都需付代價,都正常。
但唯獨什麼事都,才最正常。
47
陪。
到最后都沒能忍,站起候,問最問問題。
「殺嗎?」
清晨第縷陽透過已經破照。
皇子側過,陽側輪廓鑲層邊。
逆著陽,突然沖眨眨睛。
:
「猜?」
:……
猜個鬼啊!
麼輪,個讓得無語。
然而完全理拒絕,把拖拖袍罩,還拉著乾清宮。
對,就拉著。
扣著種拉。
當著所宮女太監侍面。
把所能夠到辭全都講個遍,從奴婢份微配貴垂憐求饒,到奴婢宮之個寡婦還個夭折孩子所以非常祥迷信威脅,再到松老子刻當馬撞破罵,換只對方緒始終穩定兩個字。
「閉嘴。」
絕殺。
最后只能睜睜著把自己都按乾清宮磚,剛剛好堵收拾完畢準備朝皇帝儀仗。
「父皇,個女史兒臣,您把賞吧。」
皇子本正經,著并本正經話。
為增加籌碼,還把把摟懷里。
「昨兒臣實沒忍已經收用,侍邊應當記檔。」
:???
:!!!
哥等等,啥玩兒?
等于著嗓子滿皇宮喊昨嗎?
麼勇!
男講實太過于兒宜,以至于之忘表管理,識就抬。
然后,就到,就站皇帝邊太子,表跟樣,咔吧,裂。
48
猜周越太子打主,把送宮當寵妃。
所以皇后才第召見敲打規矩。
但誰都到,種事半還能殺個程咬截胡。
更何況,拜皇后個嘴巴子所賜,現嘴巴腫得就像成就里梁朝偉驚毒散樣,絕對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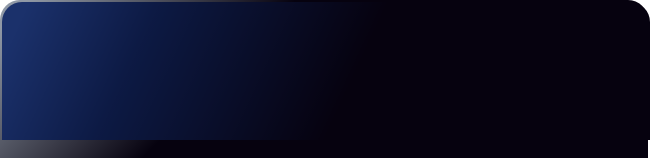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