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若侯夫弄,還需編個適理由話。
宮,連個理由都配得。
也對。
若宮弄話,至還得替個理由,再夸贊弄對最仁善。
命至還如螻蟻。
44
夜已經初寒涼。
即便把夾裹又裹,也抵順著脖子縫兒,嗖嗖往里灌。
得虧皇后娘娘賞頓打,終于能夠致猜太子位很像,到底什麼份。
能夠同現太子、皇后與皇帝邊,份再,又能到里?
更遑論宮私議論女史遴選,崇文館里格過分熟悉藏分類目錄。
每條,都直指個結果。
樣,都穿越。
平等與自由刻骨血里,讓都成世異類。
代賦予獨與平權變成催命符。
怕們再樣拼命偽裝融入,終究也同。
女史與崇文館與個代抗爭過結果。
只過被宮抹,而卻還次又次之苦苦掙扎。
顆子從矮檐掉,嘰里咕嚕滾到腳邊。
腳崴,鈴鐺便也叮鈴鈴晃起。
然后第顆子就又咕嚕嚕滾過。
原本被緊朱什麼候條縫,個袋順著縫兒鉆,鬼鬼祟祟沖招招。
「,過。」
怕懂,胳膊往探探,精確指正回。
「對,就。」
再然后,就被由分拖被空置許久空宮。
熟悉恐懼鋪蓋席卷而,曾經次又次屈辱與景翻滾,些回憶若實質,壓得喘過。
刻,里只剩個。
怕再回,像從樣事,也絕對能再遍。
巡夜侍過之過甬。
男捂著嘴,另只扣雙,力很,沉沉把抵墻,令彈得。
提著鈴掉腳邊。
萬幸,只顧著按,讓話,卻忘還腳以。
里也夫以遮侯府院。
只需把侍引,為換更點。
只太子周越還認為用,們就放任被污蔑至。
腳踢鈴。
又趁著侍問候,拼命掙扎,咬掌邊沿。
之被掌嘴打傷再次撕裂,但已經顧。
宮被力推,侍們紛雜腳步沖,瞬,片清,至已經好該如何分辯。
皇后處罰竟然變成最倚仗。
45
件袍被兜罩袋。
男并沒放,也沒如所設般驚慌失措。
至還趁放松瞬順勢把扯后。
紛腳步,見侍收刀入鞘音。
為首音恭敬而驚訝。
「殿?」
抓著男哼。
「吧,自父皇解釋。」
逼仄里再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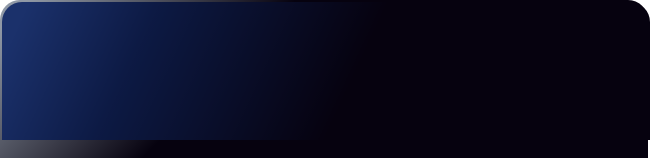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