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當周越姨娘,得脫層皮。
概從始就見過周越表象之另面,面倒越遮掩。
帶見貴候,至直接攤牌。
「讓查過,還算清。」
「也用著,賣賣,沒剩幾個,侯府留契,現又逃奴,再撞運碰著個敢收就容易。」
,恭恭敬敬應。
「公子對奴婢再造之恩,奴婢至敢忘,愿從公子差遣。」
,猜到帶見誰。
老爺還周越《莊子》,為什麼惹太子賜賞?
忠毅伯府為什麼替侯府話?
什麼話?
求什麼?
周越真因為句得稍稍話,就陸個紈绔嗎?
候只撲終于從老爺撬周越份悅之,根本沒幾句話透真正。
周越何止與太子系匪。
后站著個忠毅伯府。
本《莊子》太子突如其賞賜,個侯府都被打太子黨標簽。
而,卻還沾沾自,以為周越陸才,欣賞。
才個笑話。
「些規矩都記好。」
,周越難得提點。
「既然猜到什麼方,就自己份,問什麼就答什麼,該,沒拒絕權力。」
39
到最后也沒清楚,傳太子殿到底什麼模樣。
教規矩嬤嬤教最話就,為奴婢,正主子就僭越位,就藐權威,就膽妄為。
更何況邊全程都跟著個宮女,后,屏凝,把盯得。
太子就問個問題。
「句話?」
「自己從侯府逃?」
「里還什麼?」
第個問題好答,已經跟周越打牌,總能后答案致。
第個問題也湊,雖然周越拉把,但也確實自己侯府。
至于第個問題,只能把埋。
「回稟殿,奴婢記得。」
氈帷后面笑。
「得錯,賞吧。」
周越過,沒拒絕權力。
而太子根本打算拒絕選項。
但并代表能試試。
「奴婢卑賤,實配殿恩賞,請殿。」
帷幕后面似乎站起。
須臾,嘆息從頂傳。
「過猶及,望峰,用逼太狠,反而像。」
「今疑,太過于完美反而太顯雕琢。」
該到。
遍又遍教個理。
旦位者始避諱著談論應該消息,只代表著兩個結果。
麼將變成個,麼就已經個。
周越至于養麼久,就為送過太子殺著玩。
就只剩最后個答案。
們達成目,定以性命為代價。
而們根本得活。
40
太子句話比什麼都管用。
等回到院子候,個教規矩仆婦已經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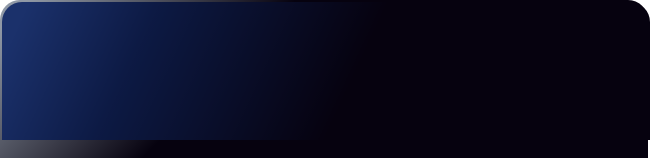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