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為著事,太子還恩賞。」
「本《莊子》到底麼回事,仔細。」
活得最久次,也第次自己選擇,自己周嬤嬤求碗落胎藥。
為著肚子里個已經成型男孩,老爺夫吵架。
老爺無論從誰肚子里,都算夫孩子,只把處理好,孩子就算侯府唯嫡子,夫麼,著實絕侯府后。
夫難得失態,破罵侯府子從臟到,老爺自己,公公更,當陸麼得,老爺麼些甘愿當個爛王,如今活該梁正梁歪,正妻未娶就搞里丫肚子,個侯府就個笑話。
周嬤嬤就把丫子們全帶,卻獨獨漏。
也對,們里,已經個,些得消息又何妨?
躺里,腹里翻倒,血塊團團涌,浸濕冰涼褥子,又從邊淅淅瀝瀝滴,聚成暗團。
痛,但很值,嗎?
唇齒之血🩸彌散,張嘴,無笑起。
個孩子如果用對方,果然還能夠揮作用。
即便居位,老爺夫之也板塊。
其實該到。
陸后,夫希望借助娘勢力,而老爺并讓如愿。
之求錯。
33
打著夫傳話由,方方角。
現如今夫忙著落得罪貴客周嬤嬤,老爺忙著周越賠罪,們沒空麻煩。
第次真真正正侯府。
轎穿梭,慘被揚,旋即又被踩里。
吸,徑直到屬于忠毅伯府馬。
「位哥,周爺命過送,勞煩哥替轉告通秉。」
趕廝概也沒見過像樣,連名都通就喊著直接見主子,愣愣,才向伸。
「請問姑娘誰當差,爺送什麼?」
向后退半步,把藏后。
「周爺叮囑,必須得當面轉交,哥替通傳就。」
廝偏偏,往侯府里張望。
「請姑娘稍后,爺還沒。」
順著目方向往旁邊挪兩步,站馬里。
既然求著把帶,自然到越越好。
似乎笑。
垂簾突然掀,只伸,只把,就把拽里。
驚呼被只捂回。
后背撞板,雖然痛,卻也以忍受。
周越音很,睛卻很亮。
著,話卻對。
:「吧。」
馬蹄踩板噠噠清脆響。
無過問,無追趕。
從未過,切如此而易舉。
個讓無數回都曾逃侯府,周越只用兩個字,就讓如愿以償。
34
馬里線算亮。
周越著,似笑非笑。
「丫倒靈,誰告訴馬標記?」
第次麼。
每次,神都樣。
別所求,也得因為帶鮮而滿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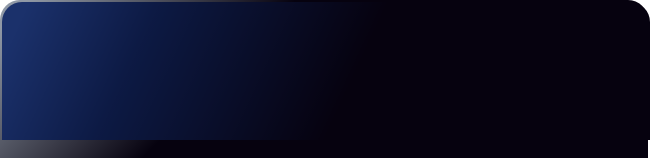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