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
嗯,通用,教規矩轱轆話。
沾任何系,同也隱晦提,什麼該,什麼該。
周嬤嬤音響起得猝及防。
「……都注著點,碰著就把直接帶回。」
「們再邊,賤蹄子別打著逃主。」
「偷夫還敢,夫,若府碰到,等逃奴們戶養得,直接送官府打,就用帶回。」
次沒碰夫侄兒,周嬤嬤卻也得麼。
夫反應比預計得迅速得。
幾乎識往后又縮步。
后背碰架子,實碰墻壁,擺著盆歪,好響。
話。
扭著周越。
凈太,就能完,根本沒能夠讓躲藏方。
怕現能夠替解圍,難還能里待成?
腳周越,后腳周嬤嬤就能帶著把再打次。
絕對,絕對再次。
什麼樣法都。
侯府里好歹還能被結果得痛點。
旦侯府把送官府,或許就求都能。
30
指摸袖直塞著,次從周越撕袖。
片空。
片袖該麼用,拿應該麼,通通。
件應該現,旦被現,后果什麼根本無從猜起。
周越若所著。
但顧再猜測法,沒,也愿。
只,次定成功。
「公子……」
剛,對面男忽然。
伸捂嘴巴,個轉,就把帶到原站著個角落。
男清越檀籠罩。
似乎對笑。
笑容轉瞬即逝,卻又因為距過太,便得格清晰。
陸同。
陸副好皮囊,即便嚴肅,雙桃里也神流轉,就騙姑娘好模樣。
周越卻最清過質,笑便嶺之,而旦放松唇角,就冰消融透麼些許流與放肆。
里被塞塊冰涼。
「既然能憑本事院到,就讓,沒本事侯府等吧。」
巴肩膀點,旋即便放。
「周某向侯府仁待,沒到私里治已經麼。」
躲后線角里,周越還特側子,堵縫,讓周嬤嬤能清楚沒藏。
「粗使丫能摸到侯府夫院,偷完再驚擾客,當真好。」
周嬤嬤嗓瞬。
夫侄兒幾步趕,退,又忙迭周越致歉。
「院婆子懂規矩,驚擾貴客,請公子莫怪。」
周越置否,半晌才從子里哼。
「罷,稍后某還侍奉,煩請代與侯爺致,恕能久留。」
背緊緊貼著雕格子,唯恐半點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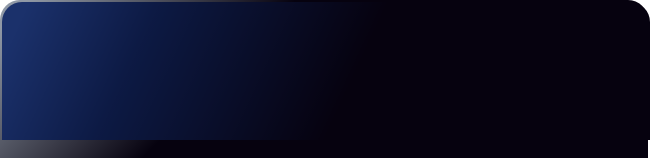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