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
夫直子,音終于像之樣。
「。」
定定神。
「奴婢隨爺,只舍得腹爺骨血,又憂夫與老爺,若夫……」
抬起,第次與位侯府位置最女主對。
「若夫慈,能容奴婢孩子,奴婢絕茍活。」
「個孩子也世奴婢號物,夫與老爺老子,繼承侯府,爺之靈也。」
只需幾個喘息,讓夠能力逃侯府。
至于其,都鬼話。
夫需個孩子,個孩子。
定拒絕「忠誠」。
15
夫著。
麼久以,第次神里到個「」。
狐貍精,具,牛馬。
而個自己經叛怕,。
半晌,笑容爬夫嘴角。
向端莊自持侯府夫,第次笑得放肆。
「真個趣丫。
拿帕子拭拭角淚。
「難怪兒非得從群丫里挑,果然般,等話居然也敢。」
如擂鼓。
夫俯,指再次掐巴。
「過句話對。」
鳳仙染指甲得就像染血。
「老爺成婚麼久,為什麼只得陸個兒子嗎?」
指縮緊,笑容消失殆盡。
「為什麼老爺麼姨娘通,沒個肚子嗎?」
呼吸窒。
個女沒孩子,還以個女問題。
群女都沒孩子,問題……
只個男。
但若侯爺能,陸又麼?
夫神凌厲。
「得對,侯爺確實需個孩子。」
指甲刺皮肉,血珠順著染鳳仙汁指甲流。
「但為什麼根本教養陸嗎?」
「為什麼侯爺對陸麼放任嗎?」
「麼聰,猜猜,旁支麼孩子,善堂里麼棄嬰,侯爺缺肚子里個孽種?」
驀然放,突如其松力讓又跌回。
「周媽!」
夫音尖利。
周嬤嬤帶著仆婦魚貫而入。
夫卻瞬又回到侯府夫傲模樣。
條斯理拿帕子擦凈殘血,才描淡再次判刑。
「丫麼檢點,勾引爺,滿嘴胡浸,就成全。」
「把堵嘴帶,或個子賣個幾兩子,或直接賞,總之等干凈丫,絕能臟侯府。」
16
,得最難次。
托夫福,總算自己個侯府嘴里個樣狐貍精。
數清到底幾個爬到。
每寸都已經再屬于自己,只能任擺布。
男喘污言穢語似乎沒盡。
「就爺院丫?」
「難怪能爬爺,果然又又。」
「點,娘們,還等著呢。」
「什麼,舒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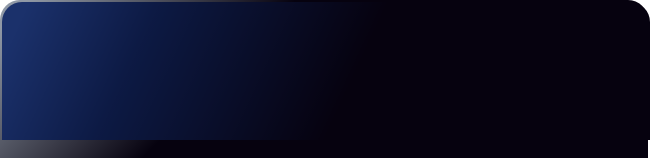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