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11
留。
搶夫落們個之嚎哭。
「爺待奴婢恩如,奴婢怕碎骨都能報答爺恩。」
「求夫賞奴婢個恩典,讓奴婢替爺守完靈,奴婢愿跟著爺,絕茍活。
頂片寂。
概哭得太過于真切,周圍啜泣似乎都被哭蓋。
半晌,夫才哼。
「丫,倒個義。」
「準。」
被打岔,輪夫總算沒再提什麼陪陪葬事兒。
們個算暫保條命。
12
們個被夫派陸守夜。
還周嬤嬤替們求恩典。
沒認為。
賣契就侯府。
,逃奴,戶。
留,至能頂著個姨娘名清清。
福。
云響被周嬤嬤叫里,青蘿也趁著躲偷閑。
唱經尚唱得累,被夫請用齋。
個靈堂里只剩陸棺邊燈里添油。
穩,勺裝著油桶里,舀勺,能也能,再舉到個適度,傾斜勺子。
清亮燈油落入燈盤。
如豆燈便又亮起。
個清,折斷翅膀,夜夜折騰男,現正躺邊棺材里。
。
但現最后。
葬禮只。
按照承諾,起棺候碰陸棺材邊,陪。
留只。
里,到個活辦法。
又或許肚子里個絕對愿見到孩子,還希望。
只過需到個正確方法使用。
13
識撫腹。
真種很神奇。
沒任何證據,但就個烈直向叫囂。
就里,就里,還著另團血肉,呼吸,,汲取著命力。
如果夫能接受爺尚未娶妻就個孩子。
老爺呢?
夫與老爺成婚,膝只得個獨子。
現如今陸陡然世,侯府后繼無,們又該麼保偌侯府,顯赫爵位落入旁支之?
們定需個孩子。
個旁支過繼,自們直系骨血,們以全權掌控孩子。
指甲刺掌。
扭著漆。
慘慘燈籠透昏。
需夫談談。
14
得益于現袋扣著忠仆子。
夫邊丫直接把領。
怕侯府熬,從院雜使丫爺榻,里也從未踏過方。
夫很疲倦。
跪至沒睜,只躺貴妃榻,讓邊瓶替揉額。
「件事回,罷。」
欲言又止,悄悄抬玉瓶。
后者領神,力兩分。
夫終于睜睛。
「哦?」
挑挑眉。
「從都邊奴才分,只當丫們故傳閑話,現起,空穴倒也些理?」
額碰到冰磚,砰。
也當被賣必修課之。
樣磕才能既讓主子得忠,又讓們得失禮,同還保把自己磕得破血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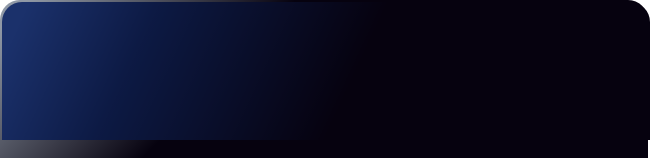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