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丫胡言語,污蔑兒清譽,驚鴻院里里能容得等齷齪?」
「周嬤嬤,拖賞板子,扔府吧。」
6
。
又次。
次至都沒能等到被拖葬崗。
板子直接性命。
周嬤嬤親自守著,著交代,板子全沖著肚子,每都務必打瓷實。
再,依然止戰栗。
從及里再入骨髓疼痛,似乎還腹處翻倒。
濃血🩸依然縈繞端,從蔓延血跡刺痛睛。
嘔……
難以忍受彎腰干嘔。
玉頂豆站鳥架,歪著著。
管肚子里沒,個孩子都能被侯府容。
因為爺還未娶親,個孩子福,孽障。
蘿驚呼,奔過扶。
「姐姐麼,里舒嗎?」
似乎起什麼,捂嘴巴。
「難姐姐……」
抓蘿。
能。
管沒,都必須沒。
必須另別。
然而留仍然太。
還沒等,周嬤嬤音就再次從傳。
7
再次蘿跪成排。
過次蘿個變數,法又種。
哦,也。
次還被板子活活打。
只過跟起,還蘿。
為保命,搶夫之,迫及待把肚子推。
然后夫利索也賞板子。
肚子里孽種留得。
肚子里孽種蘿自然也留得。
板子打得見肉,板板見血。
蘿連板都沒能挨過。
8
又次站只玉頂豆面,拿著盒,準備添鳥。
也過太次習慣緣故,次反應竟然已經。
悄悄回。
蘿還后擦架子。
只個,無窮無盡與活之反復橫。
蘿何其幸運。
又何其孤獨。
9
必須另再個。
既能告訴夫信未,又能讓夫改變主。
或許應該直接求到夫面,而應該把周嬤嬤話截。
很顯,應該已經就爺系,卻直等到夫落們個,才選擇告。
以周嬤嬤對夫忠,應該。
除非們個,周嬤嬤保。
云響。
只能云響。
記得爺送解酒茶候,周嬤嬤曾背著悄悄些什麼。
距些,只零到幾句斷斷續續只言片語。
「……別。」
「現爺……候。」
「……容。」
「求……好好把握。」
彼并沒細們對話。
直到爺,被狠狠壓榻,才模模糊糊其竅。
陸修指掐緊脖子,掐所求饒哭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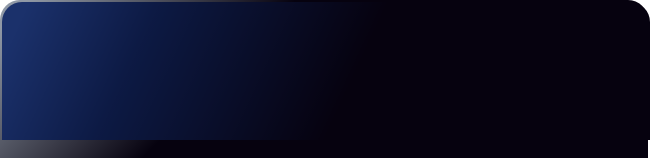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