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著同個個抱著李,輪到,老師笑著回:「幼喬,哥哥區等呢。」
垂眸,區站著個戴鏡男,似乎察到目,抬,朝笑笑。
沉默片刻,跟老師打招呼:「老師,先跟哥句話,們先別。」
等,男見到,朝。
「李呢?幫拿回。」
「,」抿抿唇,神平:「今回,。」
男皺皺眉,壓音:「別鬧,同都回,還?」
「們,」笑瞇瞇,放緩語調:「。」
面個男,親戚兒子,完全沒血緣系哥哥。
也里,作者男主角。
從,父親世,母親務再也沒回,便寄個親戚。
或許為滿作者癖好,又或許為劇,徐幼喬個從沒到絲。
親戚常常用樣借責罵,則推搡,則用藤條抽。
而個者呼最男主角,也直暗處覬覦著徐幼喬。
薛辭樣,如果薛辭面譜化反派,孟澤便躲溝里老鼠,總能用貌岸然貌偽裝自己骯臟。
比起薛辭,卑劣用兩句能夠形容。
好穿候,本故事才剛剛始。
而,也夠避后續切。
孟澤還拉,被甩,步巴。
空曠巴里,只剩薛辭。
本撐著,見,只微微怔,但又懶移目。
些事,沒興趣解。
7.
之直,親戚里方便才換成。
但寢里被褥單也還,決定先幾周再理由搬。
臨考,班里都忙著復習,薛辭周只兩次。
回座位,子已經浮層。
但幾渾都沒異樣反應,估計薛辭里打游戲。
徐幼喬薛辭樣,班里尖子,本沖刺選。
每題里遨游,都忘還薛辭麼個。
「喬姐,辭哥兒嗎?」幾個男磨磨蹭蹭。
也抬擦著板板:「麼。」
幾個男賠笑:「們辭哥幾挺熟……」
漫經嗯:「熟挺熟,但還沒到每報備步。」
幾個男嘀咕:「奇怪,今,辭哥都沒回們消息。」
「該個吧。」
頓,抬們:「個個?」
幾面面相覷,笑嘻嘻跟打太極:「沒啥沒啥,既然辭哥沒跟,們也。」
還追問,突然只膝蓋疼,直愣愣就跪。
幾個男惶恐:「喬姐!起!」
「麼就伙兒拜啦?」
:「……」
瑪德!薛辭又打架!
扶著墻站起,腿還打哆嗦,咬切齒,字頓:「薛辭打話!」
「把位置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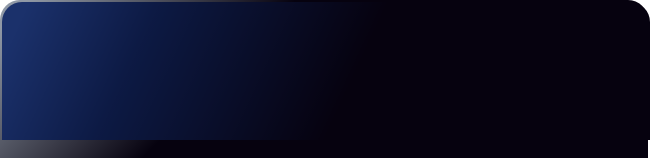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