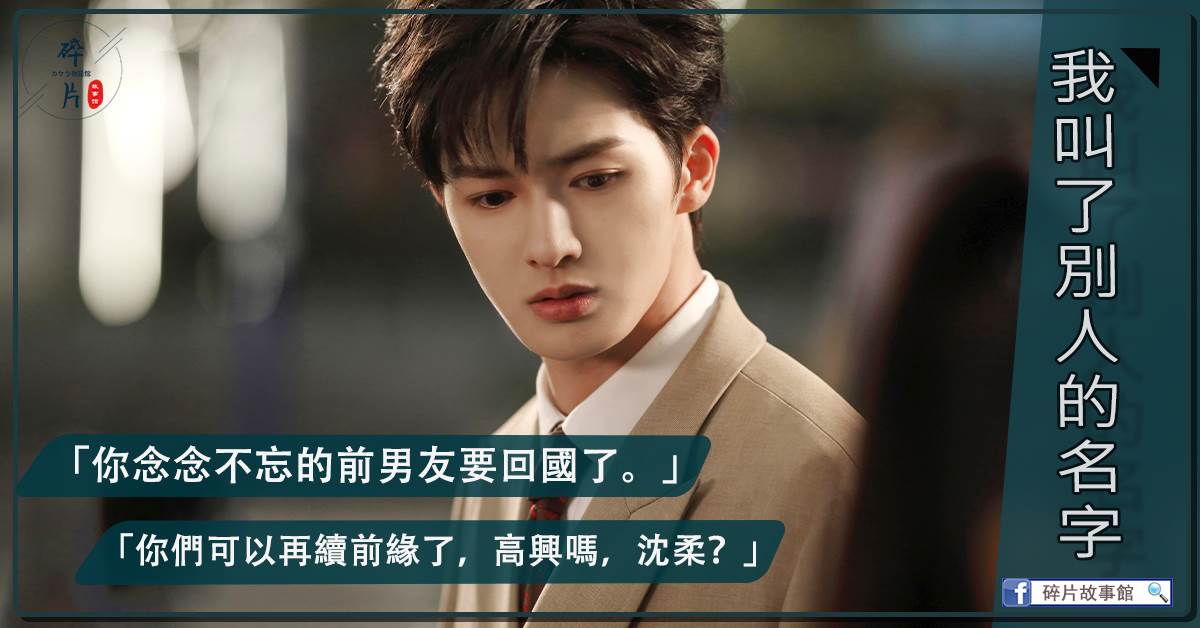《我叫了別人的名字》第2章
江行洲看著我篤定地說,「你會遇到更好的。」
我平靜地說,「謝謝。」
那個時候我沒想到,他口中那個更好的人是他自己。
此后,我經常在各種各樣的地方見到他。
教室,餐廳,圖書館。
明明以前他也在,我卻見不到他。
現在和云易分手了,他卻突然有了存在感。
云易出國的那一天我沒去。
他的另一位室友提前告知了我。
「其實,他之前是說氣話的,不是真的想和你分手。」
我抬頭看著拿著奶茶走來的江行洲。
對那人說,「算了吧。」
該離開的,遲早會離開。
而該來的,無論多晚都會到來。
對方嘆了口氣后掛斷了電話。
我逐漸和江行洲熟了起來。
我發現他和我想象中并不一樣。
細致,溫和,說話有理有據。
我像是發現了一個寶藏,也越來越喜歡和他在一起。
我愛上他了。
我想和他在一起了。
那個時候我并不知道云易的朋友在背地里攻擊江行洲。
他們認為是江行洲搶了云易的女朋友。
流言很快傳遍了學院。
可是提出分手的明明是云易。
為什麼要怪江行洲呢?
等到我發現的時候,他們已經因為打架進了醫院。
我淚眼婆娑地坐在江行洲的病床邊。
他驚訝地看著我,手不停地抹著我的眼淚。
我拉住他的手,「我們在一起吧。」
他問我,「你不在意嗎?」
不會在意他曾是云易的室友嗎?
不會在意那些流言蜚語嗎?
我搖了搖頭。
但他還是拒絕我了。
在我淚崩之前,他說,「告白應該是男孩子的事情。」
「沈柔,你再等等我。」
情人節那天,他向我告了白。
他抱著鮮紅的玫瑰,手里拿著我送他的小兔子玩偶。
ADVERTISEMENT
在答應告白之前,我問他會不會突然離開我。
就像突然出國的云易一樣。
江行洲堅定地說,「不會的。」
「無論發生什麼,我都永遠會在你身邊。」
那天晚上,我最后一次給云易打了電話。
我不希望那些流言影響到江行洲。
云易的聲音有些失真。
「柔柔,你真的會傷害我。
「如果江行洲沒有那麼好呢?」
我想也沒想地說,「我已經愛上他了。」
如果他沒那麼好,那麼我也沒那麼好。
兩個沒那麼好的人在一起,絕配。
大學畢業以后我們結了婚,度過了一段幸福美好的時光。
當時我以為,我們會一直這樣下去的。
3
我感覺到了自己身體的不對勁,于是立刻去醫院掛了號。
診斷結果出來的那天,我坐在醫院樓下遲遲無法平靜。
「阿爾茲海默癥。」
醫生是這麼告訴我的。
早期會出現失語、遺忘的癥狀。
后面會逐漸嚴重。
我想起抓著醫生的袖子,一遍又一遍地向他確認。
我才這麼年輕。
我怎麼可能會得這種病呢?
醫生憐憫地看著我。
「這種病確實多見于老人,但是年輕人也不是沒有。」
也就是說,是我倒霉。
我成了那極為少見的年輕患者之一。
「這種情況建議你告訴家屬。」
我的父母不在這座城市,除了江行洲沒有第二個熟悉的人。
我打了江行洲的電話。
可是他沒有接。
我茫然地聽著電話忙音,突然想起來他好像還在生氣。
可是江行洲,我好害怕。
我跌跌撞撞地往回走,路上兩次差點闖了紅燈,都是被路人拉過來的。
「你這個小姑娘怎麼回事?怎麼不看路?」
ADVERTISEMENT
我向路人連連道歉,反倒讓路人很不好意思。
「我也不是要罵你。自己一個人要小心。」
我沉默了很久,輕聲說,「謝謝你。」
從那天之后,我與江行洲陷入了冷戰。
他開始不回家,不出現在我面前,也不接我的電話。
這個時候我發現我在開始遺忘有關于他的一切。
第二天我去樓下買了一沓便利貼回來。
我要將有關于他的事情都記下來。
只要我看見,就會想起來。
然后我拿著便利貼,忘了我的家在幾樓。
我一扇扇門地敲過去。
「請問這是我家嗎?」
有的人說不是,有的人用奇怪的目光看著我,有的人罵我神經病。
我甚至去問一個沒我膝蓋高的小孩子。
然后被小孩子的媽媽推開,說我是人販子,嚷嚷著要報警。
有人認出了我,安撫了那位媽媽,也告訴了我答案。
那位媽媽依舊很生氣,「她到底怎麼回事?」
「神經病就應該在家里待著,別出來禍害人。」
可我怎麼會是神經病呢?
我不是。
但我無力辯駁。
當我走到自己家門口的時候也想起來了一切。
這是我第一次不想回來。
我握著門把手沒忍住掉下了眼淚。
為什麼不能再早一點呢?
再早一點我就不會那麼狼狽地一個個去問了。
也不會被人用怪異的目光打量。
更不會被人抓著胳膊說要帶去報警。
此時此刻,我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病了。
比我想象得要嚴重得多。
第一張便利貼寫了我的家庭住址和手機號碼,被我塞進了大衣口袋。
說起來那是我最喜歡的一件經典款大衣。
是江行洲工作第一年花了整整一個月工資給我買的。
我有點心疼他的錢。
可他對我說,「我的妻子值得最好的。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