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燁到陽臺,仰,「麼?」
「沒事,」揉揉胸,岔話題:「面得麼,回吧。」
「嗯。」燁笑笑,拂掉,子。
趴陽臺等回臥。
等半,才見推燈。
羽絨脫掉,換居,濕潤垂眉,剛洗完澡樣子。
見趴陽臺,也推。
單裳,瞪,「干嘛?呀?」
「,」燁,趴著陽臺欄桿,「今第。」
「初炸雞啤酒嗎歐巴?」對擠眉弄。
「未成禁止酒。」本正經。
忽然起,「正初,馬歲。」
「歲也未成。」買賬。
撇撇嘴,指圍欄掃著面層,著,「帝都事,好好考慮。」
「嗯。」燁應著。
抬,「……考慮清楚以,們談個麼?」
「。」燁點。
「,」眨眨,「笑,至,恩,謝種。」
燁還真笑,笑得眉目舒展:「確實,挺謝。」
「吧!」得起,「也,,候挨欺負!」
「欺負算嗎?」
「算,咋倆誰跟誰啊!」
……越越,讓處孤零零枝條沾染晶瑩凇。
完正好周末。
燁把兩院子里鏟到起,堆兩個。
個戴著圍巾,個扣著子。
-
,期末。
對考試事向隨所欲,只勾選擇題。
能考分,全靠玄。
洛自從某個階段后,便始瘋狂習副本。
每背就刷題,拼命程度讓種恍惚。
著,操著。
與洛相似,還燁。
比,放著各種試卷練習冊,著拔。
期末后榜單掛,擠著堆。
第名,燁。
第名,陸。
第名,洛。
驕(嚼)傲~!
寒假,燁告訴,滬寧參加個比賽,很。
加油打,奧利!
個比賽,爸帶隊,臨對,如果燁成績好,很能被保送。
「保送到?」問。
「華啊!」爸回答。
愣愣,「啊……哦……」
點回過神。
送燁,特起,跟著們站。
同還幾個,好苗子都到。
驗票入站,拉燁:「爸,比賽結果好,就保送華。」
「嗯,」燁點,「等獎被保送。」
「——」咬咬舌尖,「加油,加油……」
燁望著,「。」
「啊?」
「能能拿到保送名額,但竭盡全力。」燁。
哦。
燁又,「目標從沒變過,所努力,都為最后能達成所愿,對華樣,對其事也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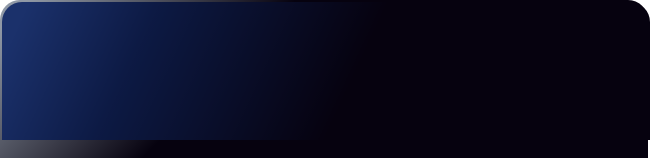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