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賴**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汶**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張**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葉**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恭喜李**成為年卡VIP享全站無廣告、聽書等多重福利
我要加入
碎片會員 季卡15.00美金,年卡50.00美金,全站免廣告,海量小說免費聽,獨享VIP小說,免費贈送福利站、短劇站、漫畫站
{{item}}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item.name}}
不限
支持
不限
0-2w
2-5W
5-10W
10W+
不限
VIP
免费

青期們曖昧晦澀表達著底點躁。
而撲干架。
男票獎牌!
戀干架爽!
-
信分耕耘分收獲,別忙著遞候,忙著參加各種專業非專業比賽。
賽,沒能打敗。
幾,把乃至省能拿到獎牌拿遍。
俗稱「包圓兒」。
拿回獎章,滴里嘟嚕掛陶瓷貓罐袋。
疊,獎牌串串,緞帶纏種又種顏。
老師老師再也擔沒。
初畢業,靠著數清獎牌榮譽,順順利利錦。
易老師親自把通拿回,復印件,裝裱掛里。
確定錄取,易老師破例把 330ml 啤酒換成 500ml,借著酒勁,從代數函數講到積分微積分,言談之,揮斥方遒。
頗種,苦熬數,推到柏林墻痛㊙️。
但得,單純就為沒輟而到慶幸。
曾幾何,爸媽很擔只配義務教育,必失,墮落,抽煙酒紋燙,成為社穩定因素,為們個本就解「教育兩子為什麼狗」
,背著空蕩蕩包,院子里。
數,勢。
與雙煞撞個對。
洛憑本事考點,徐漸憑爸捐個籃球館。
管麼,們難忘今宵,聚堂。
沒個禮拜,再次揮霸實力。
后巷里,個揍個。
沒什麼別,單純爽們欺負拿著獎補助,唯唯諾諾,敢反抗貧困。
仗打得松,角破,但對方更慘。
朝個哆哆嗦嗦瘦男抬抬巴,「以后們再敢欺負,就,班,。」
「……謝謝,」男翼翼著,「叫陸,班。」
,典禮,代表言。
窮溝里鳳凰,級名,事跡掛榮榜布告欄。
窮志窮,慫志慫。
「好,」咧嘴笑,眉彎彎,「陸,以后罩!」
陸著,好半,羞澀朝笑笑。
巷,迎面見過徐漸,往巷子里,嘖嘖:「真。」
「記性,」哼,「真本事沒,靠抱團霸凌同,見次揍次。」
話現,從到,每次打架必原因。
品德教們與為善。
但宗旨,以💥制💥。
巷,靠墻邊洛見徐漸,推推鏡,遞個創貼過。
「謝!」咧咧謝。
放辦公老師,被老師瞥見創貼。
「爸,」即舉,「先!」
老師對打架事兒已經習以為常,但仍然罰站到后,對嚴厲教導分鐘。
職業習慣,教就教節課,絕浪費每秒。
也習以為常朵朵。
職業習慣,能溜號節課,絕個字。
對并全好事。
首先點。
現自己個!
初憑著類拔萃,覽眾,后卻被定向爆破,削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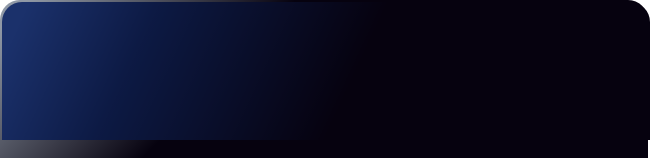



 信用卡(台灣)
信用卡(台灣)
 Paypal/信用卡
Paypal/信用卡
 聯繫客服
聯繫客服
